
六
1959年5月,《四百击》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标志“新浪潮运动”诞生,各大媒体开始用“新浪潮”这个词来描述法国的新电影运动。但到了1960年,方兴未艾的“新浪潮”就遭到全国媒体的声讨。
这 一年,“新浪潮”导演先后遭到商业失败,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Tirez sur le pianiste)只有70000人次入场,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Une femme est une femme)不到65000,夏布罗尔的《献殷勤的人》(Les Godelureaux)是53000,雅克·德米的《罗拉》(Lora)只有35000,而戈达尔的《小兵》(Le Petit soldat)则因触及阿尔及利亚战争则根本没通过审查。随之而来就是各大媒体的“声讨”,人们公开发表文章抨击“新浪潮”给法国带来的市场逆流和负面影 响。编剧米歇尔·奥迪亚尔(Michel Audiard)(今天导演雅克·奥迪亚尔的父亲),在当年特吕弗曾参与论战的刊物《艺术》周刊上发表文章,声称“新浪潮已死”。著名电影杂志《正片》 (Positif)则做了一期“反新浪潮”专题。萨特的助手让·科(Jean Cau)在《快报》(L’Express)上发表激烈的批评文章,认为新浪潮“这些年轻导演说了什么?他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
在这个声讨四起、 危机四伏的时侯,特吕弗可以像夏布罗尔和罗麦尔那样选择沉默,因为他个人认为“新浪潮根本不存在”,“新浪潮”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但就在“新浪潮” 的口碑即将被摧毁时,特吕弗主动承担起“新浪潮”的名义,对那些文章予以反击。他1959年底在《时代符号》(Signes du temps)杂志上写到:“应该像占领时期的犹太人那样,为自己属于‘新浪潮’而感到骄傲。”1961年10月,特吕弗主动接受《新观察家》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的访谈,在腹背受敌的文化格局中,主动扮演“新浪潮精神”的捍卫者和阐释者,向责难发起反攻。
在这 种局势下,只是笔头上的论战已经说明不了问题,人们要“新浪潮们”拿出令人可信的作品。但在那时,新浪潮导演普遍受到制片商的怀疑,特吕弗的新片《朱尔斯 与吉姆》(Jules et Jim)一度陷入投资危机,他甚至对摄影师提出中途放弃拍摄,但在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作曲乔治·德莱吕(Georges Delerue)等人支持下,特吕弗还是用精简的成本完成了影片拍摄。这时的特吕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影片必然成为下一轮论战的靶子。可是《朱尔斯与 吉姆》拍摄简陋,资金短缺,拍摄几次受阻,特吕弗预感到自己将面临空前失败。1962年春,在举行完私人放映会后,特吕弗心情很差,他给好朋友海伦·斯科 特(Helen Scott)的信中写道:“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差的电影”。
但是,《朱尔斯与吉姆》并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影片随即受到让·雷诺阿 (Jean Renoir)、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等导演的大加赞赏,两个人分别给特吕弗写了两封长长的信表示祝贺。但对特吕弗鼓励最大的,是来自小说原作真实女主人公、75岁的海伦·海 塞尔(Helen Hessel),她看过影片后给特吕弗写了一封信,向这个年轻人表示致意。在风格上讲,《朱尔斯与吉姆》不是百分之百履行特吕弗论战时提倡的“作者”原 则,他甚至站到了他曾批判的“优质电影”里,影片尊重小说原著的时代气息,并让这个较为敏感的“三人之爱”题材变得浪漫、纯真、感人。
影片上映后,舆论界“围攻新浪潮”的局面迅速扭转,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还是《艺术》周刊,再次转换枪口,称赞《朱尔斯与吉姆》是“温柔与智慧的相遇”。曾发表让·科抨击新浪潮文章的《快报》,也纷纷站到特吕弗这边来,称《朱尔斯与吉姆》是“第一部真正的新浪潮电影。”
这一次,特吕弗不再恪守自己的理论教条,而是忠于电影所能接纳的所有表达能力,《朱尔斯与吉姆》兼具新浪潮风格和法国传统电影的魅力,终于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影片上映后在法国形成一股热浪,影片人物所穿的10年代服饰造成了巴黎时装界的复古潮流。
七
在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前,电影界率先发生了“捍卫亨利·朗格卢瓦”事件(L’Affaire Henri Langlois),从某种角度讲,从3月开始的法国电影人与索邦学生在电影资料馆的抗议示威成为“五月风暴”的前奏。
当 时特吕弗的《偷吻》(Baisers volés)即将杀青,但对特吕弗来说,捍卫法国电影资料馆比自己的电影更重要。2月,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电影资料馆改制,卸任朗格卢瓦的馆长职务,特吕弗义无反顾地参与到“捍卫朗格卢瓦” 运动中。我们在贝尔托卢奇的《梦想家》(The Dreamers)里可以看到当时示威的情况,到处飞着传单,让-皮埃尔·雷奥(Jean-Pierre Léaud)在索邦大学高声朗读抗议书,特吕弗则走在游行的最前排。
在五月的戛纳电影节上,特吕弗联络阿兰·雷乃、克洛德·贝里、罗杰·瓦丹、克 洛德·勒鲁什等导演在戛纳举行一场捍卫电影资料馆的新闻发布会(13日),成立了“法国电影一般状态委员会”(Etats généraux)(15日),委员会迅速得到参赛导演(米洛斯·福尔曼、阿兰·雷乃、克洛德·勒鲁什)、评委(马勒、罗曼·波兰斯基)及后赶到戛纳的导 演(戈达尔、里维特)等人支持。18日早上,在戈达尔的建议下,特吕弗带领青年导演们占领了电影宫正厅,他们登上舞台,宣布电影节中止,结果与电影节组织 者在舞台上发生剧烈冲突,导致戛纳电影节历史性地流产。
但“五月风暴”之后,特吕弗唯一参与的政治运动只有一个:继续支持亨利·朗格卢瓦,除此之 外,他没有参与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他“不相信乌托邦”,以满满的日程表驱使自己“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他两年拍了4部电影,“以拍摄的方式悄悄地 远离社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戈达尔开始嘲讽特吕弗“上午的商人,下午的诗人”,最终在《日以继夜》上映后两个人公开决裂。
八
在整个70年代,特吕弗没有正面回复任何一个朋友的嘲讽和批评,也从未离开电影。
他 不参与左翼运动,拒绝在政治艺术家名单中签名,也拒绝参与各种形式的政府官方活动。他虽然后来与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等知识分子在大选中联合声援密特朗,但他拒绝与密特朗出访国外。在这个时期,特吕弗始终坚守一个“电影人”的准则:不浪费制片人的钱,坚持中 小规模拍摄;拒绝承认自己是艺术家,从不放弃观众;不批评电影同行和合作者;拒绝做任何电影节的评委;没有在任何政府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甚至拒绝做法国 电影资料馆馆长。特吕弗后半生唯一的政治经历依然与他天生俱来的迷影色彩有关:他做了3年法国电影俱乐部协会的会长,为继续发展迷影文化而工作。他当时用 画家马蒂斯(Matisse)做比喻,“马蒂斯经历过三场战争,但没有参与其中任何一个。而是在画鱼、女人、花朵和窗外美丽的风景。是战争造就了他生命中 那些无聊,在充满危机的事件中,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成百上千的画布。”8对于特吕弗,电影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他在避难所里度过了整个70年代。
在 这个背景下,我们再回到1981年《最后一班地铁》最后那场戏,仔细体会玛丽蓉在战争年代将政治与艺术同时“高高举起”的真正含义:特吕弗动荡的人生好比 影片中的战争背景,玛丽蓉苦心经营的狭小剧院好比特吕弗在各种纠纷和争论中坚守的电影世界,玛丽蓉不愿意离开巴黎而投身抵抗运动,就像特吕弗宁愿与世界周 旋,却对电影始终不离不弃。他以捍卫电影的赤诚和激情让他的选择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正确”,最终获得拥戴。这种精神就是苏珊·桑塔格曾经宣告已经死亡了 的迷影激情(cinephilia)。特吕弗始终想远离政治,在电影中营建一个理想的艺术世界,像玛丽蓉那样始终坚守在最难周旋和权衡的世界,维护电影的 生息。他虽然提倡“作者电影”,但始终不远离公众(影迷),他绝大多数影片的票房收入都在年度总排名的前30名之内,这个成绩远远超过其他的新浪潮导演。 特吕弗始终坚守的电影职业准则,给法国电影后辈留下了良好的传统,这才是特吕弗留给法国电影的真正传统。(完)
注:本文曾发表于《文景》杂志,转载请注明。原文中的注释已被我省略,重要引文均来自塞尔日·杜比亚纳(Sergie Toubiana)和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que)合著的《特吕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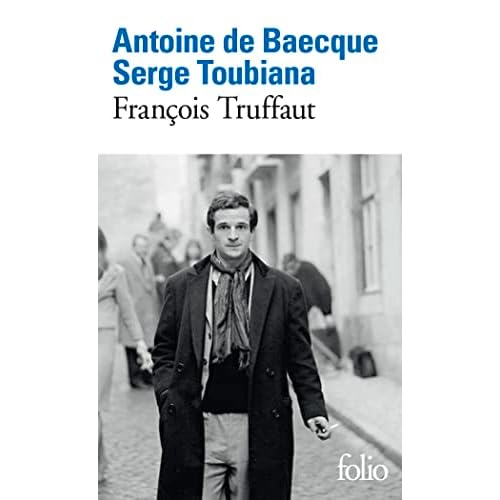
终于等到更新了,更佩服特吕弗了
这是我最近看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八”那一部分的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写得真好
一直以为戈达尔是一位很真的导演,对特吕弗的个人评价不如戈达尔高。
今天才知道,原来特吕弗热爱电影的心这么诚挚。虽然要一个纯粹的电影环境很难的,虽然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避免的要戴上某种意识形态,但是对于特吕弗这种老老实实做电影的态度还是很感动。
“不浪费制片人的钱,坚持中 小规模拍摄;拒绝承认自己是艺术家,从不放弃观众;不批评电影同行和合作者;拒绝做任何电影节的评委;没有在任何政府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甚至拒绝做法国 电影资料馆馆长”
能做到这些真的很了不起。激进的电影实验者如戈达尔,能给电影业注入活力,但是真正使电影业不断传承下来的,还是需要像特吕弗这样始终热爱电影,恪守电影职业准则的电影工作者。
我感觉好像不管中国的还是法国的评论——就我看过的那些来说——只要一提新浪潮,都像是打擦边球,要不泛泛的扛一下理论大旗,要不就八卦讲史(当然新浪潮的八卦都异常好看)。
文化上正确和政治正确的分歧到底在那里?如果要我理解的话,T恰恰是政治上正确,而G搁到文化里,就像法语里讲politiquement correct,最普遍的理解就是指一种容易被接受的,不尖锐的表达方式。
当然我这么说有点像狡辩,曲解了虎皮的概念,虎皮这里文化和政治是非常明确的两个概念,字面上的概念,但我看完后总觉得痒痒的,想来一拳头最后只是一片羽毛轻轻掠过,个人对T不算太感冒,但他的确有几部让人着迷的作品,想不通的是,如果热爱电影,不谈政治(字面上的政治),不放弃观众既是“文化上正确”,那么是不是大多数好莱坞导演也可以归入此类?
到底什么是“文化上正确”?什么是“正确”?戈达尔政治上“正确”么,因为他说了电影就是政治,所以他的电影就只是政治?当我们谈起新浪潮,我们究竟该谈作品还是谈人?“坚守的电影世界”,到底谁在坚守?如何坚守?
一堆问号,因为脑子里真是一片浆糊,TNND,电影是什么呢?
殊不知这篇文章有多少句子都不是说给史实和法国听的?其实在法国,根本无所谓“政治上正确”,这种话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它不是集权国家,就无所谓驴正确,或者象正确,至于那些概念,教科书上有写,尽管反反复复欺欺掺掺弃弃,总还写过,MARS,你要听弦外音。